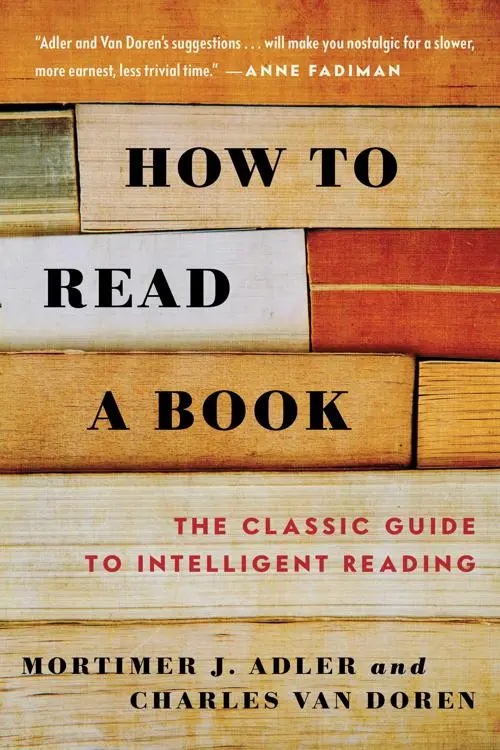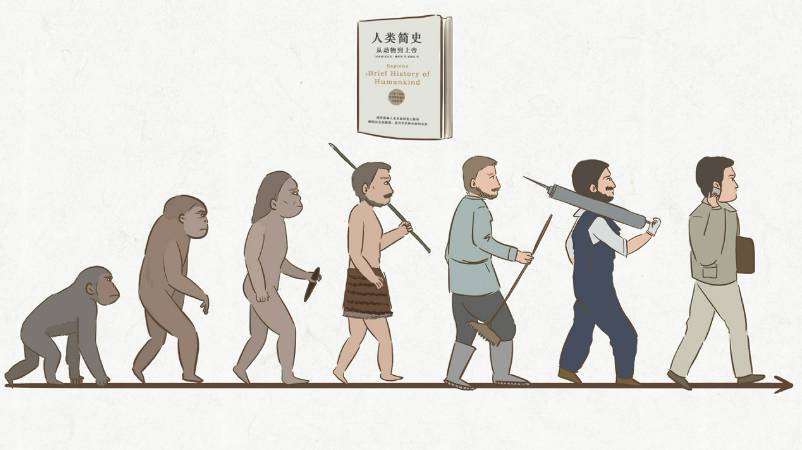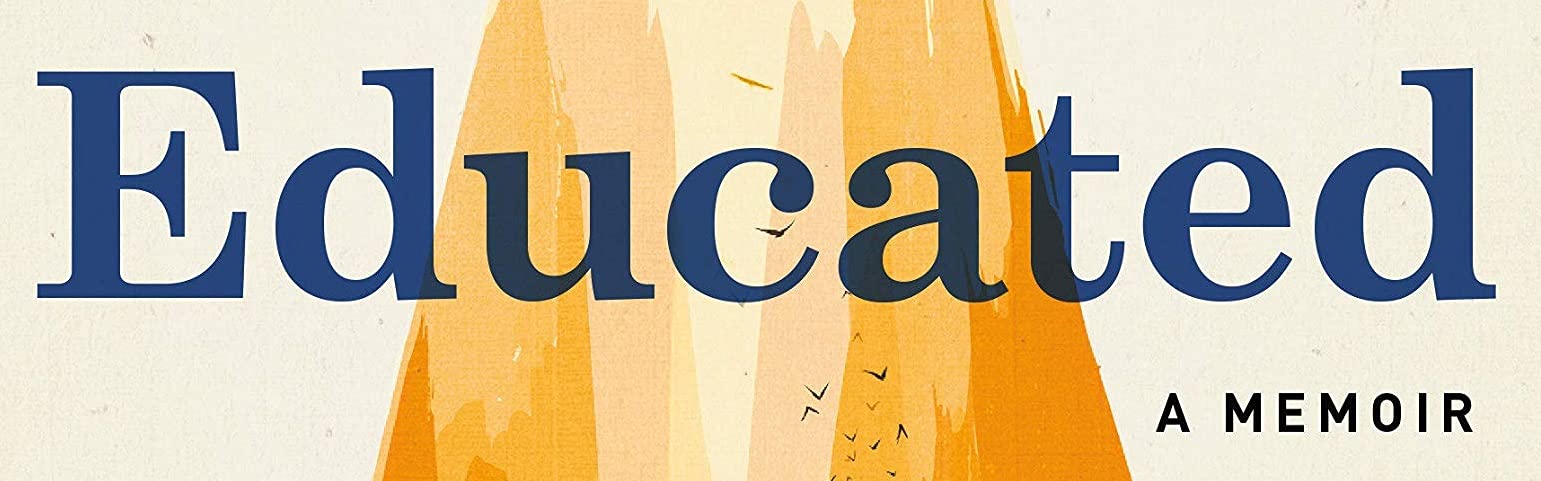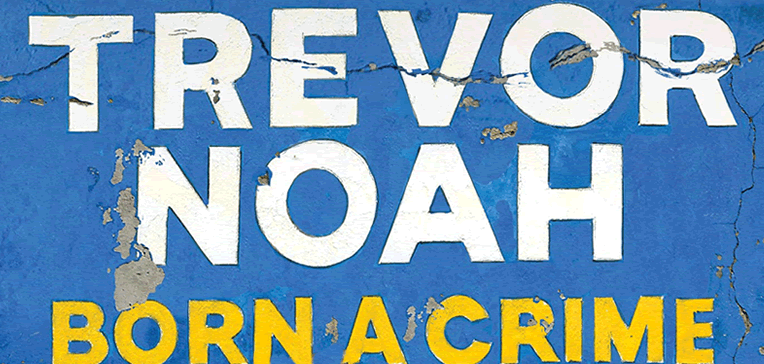日记(十二)
日记 八月十三日 17-25° 多云 前些月偶然间读了网红作家吉井忍的网红作品《东京八平米》,看完才发现其实并不是关于“极简主义”的论著,而是一本多少充满着一些炫耀感觉的散文集。读到《东京寻房记》一节时,心想,“就这水平还好意思显摆”,于是模仿写一段。 写这篇文章之前,忽然细想⾃⼰到底住过多少房间呢?屈指算来⼤概有二十四个,⾃⼰都不太敢相信。 据说⽇本⼈⼀⽣平均搬家次数是3.12次,住过的都道府县(⽇本⾏政区分)数为2.13个,住过三个以上都道府县的⼈有三成,没离开过出⽣地的⼈也有四成。从这些数据推想,⼤部分⽇本⼈会长期定居在⼀个地⽅。我有时候⾛在路上,尤其是路过⼀个很陌⽣的地⽅,从别⼈家的厨房飘来阵阵味噌汤⾹味的傍晚时刻,突然会很羡慕他们的人生:熟悉的环境和人际关系,发⾃内⼼的安全感和平静,⽇常左右逢源,邻居⼀呼百应。我也知道不上班的⽇⼦难免有苦闷和煎熬,我羡慕的那种人生也会有折磨,人总是想要⾃⼰得不到的东西。滚⽯不⽣苔藓,像我这样经常换地⽅⽣活的⼈肯定不聚财,但我亲⾝体验过、观察过的各种不同人生和思维⽅式,对我来说却是宝贵的财产。 回想这二十四个房间,等于回顾⾃⼰过去⼆⼗余年的⽣活。 ⾸先住⽗母家不算,从⾼中毕业开始,清华大学期间的学生宿舍“紫荆公寓”算是我在外⾯住过的第⼀间房(⼀)。毕业后搬进北京海淀区北3.5环(北土城西路)牡丹园小区的一栋老式塔楼里的两室一厅中的一个房间,约⼗五平⽶(二)。刻薄的室友是二房东,一年后不再想忍受合租生活,便搬到了不远处北三环内北太平桥的老式小区的一室一厅(三),建筑面积约四十平米,室内充其量二十平。 换工作后,依然在北三环居住,但从交通的角度来讲,通勤的难度大大增加,于是搬到了西四环四季青桥附近。虽然距离更远,但由于紧靠西四环,那时还不算太拥堵,开车通勤方便了些许。房子是两室一厅,总共九十平米,跟朋友的朋友一起合租。由于户型是客厅超大卧室很小的那种,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也就只有一间卧室,充其量十平米出头的面积(四)。 由于各种原因,接下来在公司里(不是公司附近)(五)短暂住过一段,辗转于会议室和休息室。之后跟同事合租在海淀、昌平交界的回龙观,三人合租一百二十平米的三室一厅两卫。一人独居对空间要求不大,所以干脆为了省钱挑了最小而且没有空调的那个卧室,大概十平米(六),开始了夏天每天洗三次澡的生活。到期后,在附近小区换了另外一套大两室一厅(七),一开始有同事合租,室友搬走后便开始独享整套,倒也惬意。 在北京的最后一份工作在三里屯,住在郊区着实不便,于是搬到了稍微靠东一点、近一些的望京。再加上之前反正也是一人出整套两室一厅的房租独居,虽然贵了点但体验不错,外加找靠谱室友着实很难,于是选在了老式塔楼里的一套一室一厅(八),房东是前公司其他组的同事,当时交流起来还算顺畅,但后来发现也就是中国广大不靠谱房东中的平均水平。建筑面积约50平,公摊很大,室内估计最多30,但至少是自己独立的空间,厨房、客厅、卫生间、卧室都是独立的房间,也勉强有个公共地下室停放摩托车。 2016年决定离开北京,抵达爱沙尼亚,在离市中心不远处找了个Airbnb住了一个月。房间是整套75平超大(国外不算公摊面积,所以很大)的两室一厅中的小卧室(九)。虽然房间只有十平米,但整体很惬意。房东是本地人(老家在离首都50公里的国家森林公园里),是自由职业瑜伽老师,偶尔在客厅带几个学生维持生计。一个月到期后无法续租,于是在海边的青旅找了个八人间的床位(十)住了一个月,由于过了旅游旺季,价格便宜,依稀记得一晚20还是25欧,而且基本住不满,偶尔甚至一个人没有,倒也还算舒服。考虑到当地极不具性价比的租售比,迅速买房,买在了前面Airbnb所在的同一小区,于是入住了七十五平米室内面积的大两室一厅(十一)。 在爱沙尼亚期间没再搬家,但二零一八年前往德国,自然又是一个月的Airbnb,离市中心不远的一室一厅,面积大约50平(十二)。小区环境位置都不错,很可惜不能长租,否则真是不想走了。在德国租房很难,尤其是对于刚刚抵达、没有信用记录并且语言也不太通的外国人来说。被迫之下找了个郊区的中国房东的一室一厅,大约50平米(十三)。虽然距离远了点,离市中心二十多公里,但无论是轻轨还是开车还是骑摩托车大概三四十分钟都能到市中心,对于住惯了北京的人来说完全可以接受,更何况如果开车的话路况自然是比北京好的多。要说缺点,一是在一楼,前后送的花园杂草还需要打理,实在是麻烦;二是户型,客厅太小卧室巨大,大到放了双人床、衣柜之后还有富裕空间搭帐篷。两年后房子到期,黑心房东坐地涨价,于是找了个虽然更贵但性价比更高位置更好的七八十平的两室一厅(十四),一直住到了离开德国。 疫情期间回国,先是在成都郊区的酒店进行为期两周的集中隔离,是酒店的一个房间,大约20平米(十五)。虽然住的时间不长,但毕竟是带着全部家当入住,所以也算是短暂地搬了一次家。还好有本地朋友在隔离期间就已经帮忙找好下一个长期居所,所以隔离结束后没有再次经历Airbnb,而是直接入住了成都西2.5环边的高档小区,一人独享九十平的套二(十六)。在北京大家习惯说几室一厅,但在成都大家习惯说套几,略去厅。半年后就结束了通勤的日子,开始居家办公。居家后,深受西边航线飞机噪声的影响,于是决定退租,在东二环边同事家50平的套一(十七)短暂借宿了一个月。寄居到期后,新租的房子还没买好家具,青黄不接之际,只能先后在市中心的丽思卡尔顿(十八)以及南边的W酒店(十九)过渡了一阵,然后才搬入了天府新区的套三新房(二十)。 后来赶上公司裁员,拿了赔偿之后退租,又搬去另一朋友家140平套四过度了一阵(二十一),然后决定在昆明旅居,用两辆汽车带着两辆自行车(当时只有两辆)分两趟开往昆明,先后在希尔顿花园(二十二)和洲际(二十三)各住了一阵,之后终于找到了草海边还算称心如意的豪宅(二十四)。